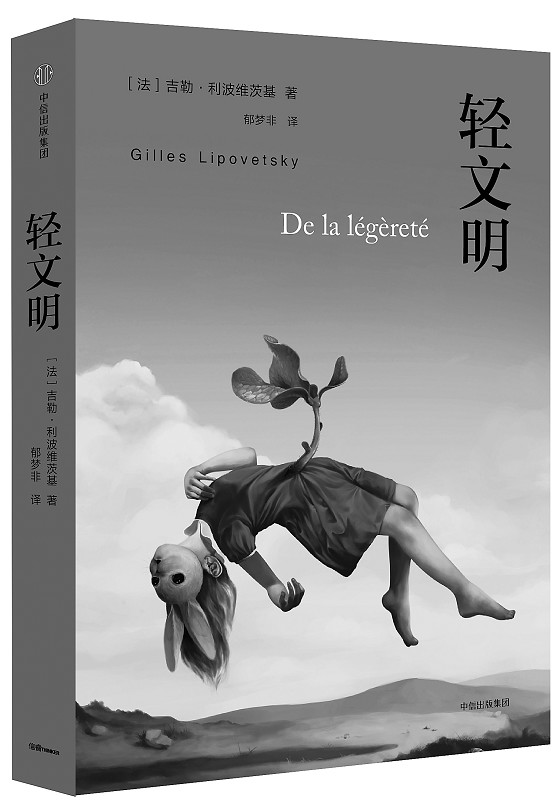|
生活不能承受之轻
作者:吉勒·利波维茨基
图:《轻文明》[法]吉勒·利波维茨基 中信出版社 2017年2月 |
|
更多>>
|
 |
 |
|
本文所在版面
【第 11 版:新消费·风尚】
|
|
本文所在版面导航
·生活不能承受之轻
|
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