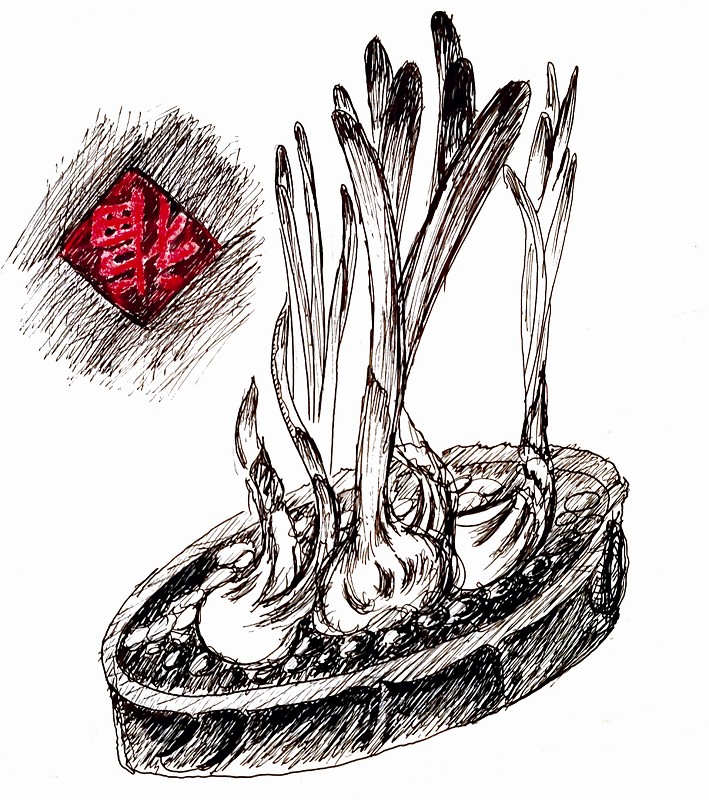|
寻找乡愁
作者:施乾元
|
|
更多>>
|
 |
 |
|
本文所在版面
【第 5 版:新春专题】
|
|
本文所在版面导航
·寻找乡愁
|

|